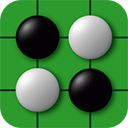1950年初春,一列由武汉南下的火车载着我军最英勇的68位战斗英雄,正风尘仆仆地赶赴广州参加表彰大会。
可谁也没料到,这趟充满荣耀的旅行却在乐昌火车站出了变故。
就在车辆停靠时,两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土匪闯入车站。
面对这些,68位战斗英雄是怎样的表现?土匪又是什么结局?
惊魂一刻
1950年3月,南岭脚下的乐昌车站,列车在一声汽笛鸣响后缓缓停靠。
车厢内,68位战斗英雄神情专注,衣着干净利落。
尽管是一群刚刚经历血战、即将赴广州接受表彰的军人,可每个人身上的战斗气息丝毫未减。
那时的他们或许没有想到,这一战,将成为他们再度立下赫赫战功的战场。
列车刚刚稳稳停下,车站入口处,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。
紧接着,车站的值班员还未反应过来,一大群手持长枪短匕、衣衫褴褛却目露凶光的土匪已经冲进站台。
这是一群久经杀戮的悍匪,他们动作迅捷,火力凶猛,训练有素得甚至不像是一支乌合之众。
面对毫无防备的乘客,他们或许是觉得胸有成竹,几人高声吼着众人抱头蹲下,剩下的大队人马径直朝列车奔来。
有人想关门,有人想逃跑,可动作再快,哪有土匪的子弹快。
就在车站陷入一片恐慌之际,那些原本打算拉开车门的土匪,突然发现,所有车门已被反锁,唯一敞开的那节车厢,是列尾的一节普通硬座车厢。
一群人蜂拥而上,准备先对这里下手,他们不知道的是,这才是地狱的大门。
冲在最前方的一个土匪,还没来得及得意地跨上车厢门槛,便猛地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掀飞。
“砰”的一声,鲜血迸溅,所有土匪的脚步戛然而止。
紧接着,一声干净利落的枪响划破混乱。
原来,这节看似普通的车厢里,坐的不是普通乘客,而是我军攻坚老虎团的68位战斗英雄。
这些人,在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战役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,刀山火海,炮弹轰鸣,他们什么没有经历过?
他们是去广州领奖的荣誉者,更是可以随时转身为刀锋的士兵。
列车内的枪声顿时密集起来,短促、迅捷、且准确无误。
车厢两侧的窗户被迅速拉开,战斗英雄们各自找好角度,从各个角度形成交叉火力。
土匪们还未来得及组织阵型,第一轮火力就将他们打得人仰马翻。
原本气势汹汹的土匪,在英雄们井然有序的反击下节节败退,毫无还手之力。
有人慌不择路地想要逃离,却被精准的射击接连撂倒,有人举枪想反击,但他的速度,哪能比得过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。
十分钟不到,枪声渐渐而止。
68位战士鱼贯而出,像是刚刚从战场撤下的钢铁之师。
躲在角落里的乘客,呆呆地望着这一幕,车里忽然有人拍起了巴掌,这是对他们的敬礼。
剿匪平乱
车站里,几名俘虏被解放军战士围起,接受着严肃的审讯。
被俘的匪徒嘴角带血,神色惶恐,却不敢有一丝隐瞒。
他们没料到,这次本该轻松得手的“行动”,竟在一个车厢里全军覆没。
更加不敢相信的是,对面这68人,用了10分钟就打的他们200多人毫无还手之力。
审讯一开始,被打怕的匪徒便竹筒倒豆子的交代出此次行动的全部计划,袭击乐昌火车站不过是声东击西。
他们的主力,足有两千余人,已从多个方向围攻乐昌县城。
此次围城的目的用心险恶,是想要彻底摧毁新政权刚刚搭建起的地方秩序。
他们要恢复他们曾经横行霸道的“旧世界”。
听到这话,战斗英雄们似乎在短暂的对视中就做出了决定。
改道入城,火速支援。
没有号令,没有动员,他们依旧保持着默契的队形,从车站徒步向县城奔袭。
这是受表彰的路吗?他们只会笑着说:“这是我们该去的战场。”
英雄们赶路的时候,乐昌县委书记陈培兴站在破旧的县政府院内,心如乱麻。
几天前,原本驻守城内的两个连队奉命开拔九峰山执行剿匪任务,整个县城只剩一个团属卫生队,还有些重伤未愈的士兵、教师与学生。
外援无望,通信被断,城中军力薄弱,形同孤岛。
但他没有逃,更不会怯。
如果这一城不守,不只是他个人的责任,更会让新政权在百姓心中的信誉土崩瓦解。
于是他做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,全员备战,保卫县城。
医院里,护士放下了药箱,接过发来的步枪,医师收起了听诊器,戴上了钢盔。
伤员中,那些能站起来的被编成了简易排队,不能行走的也被安置在战斗哨所后方,准备随时协助弹药搬运或通信联络。
中学的教师们抱着刚学会用的枪,在校园里组织学生演练掩体作战。
县政府办公厅内,几位干部干脆脱了外套,像当年战地通讯员一样,将最后一批弹药分发到各自岗位。
这是他们能做的全部。
其实陈培兴并不抱太大希望,因为这样的力量顶多能抵抗几个小时。
就在这危急关头,一声嘹亮的冲锋号突然从远处响起,陈培兴愣住了,是援军到了吗?
没错,这些人正是那68位从火车站逆行而来的战斗英雄。
他们没有重火力,没有后援补给,却凭着一腔孤勇和战场经验,悄然潜入县城外围。
他们原本的目的地是表彰大会的红地毯,却在血与火中,再一次穿上了战袍、扛起了枪杆。
这一夜,乐昌县城不再孤单。
震慑全场
县城里,土匪的主力部队已经攻至核心区域,三面火力压制下,县政府院落只剩一口气吊着,守军士兵几乎弹尽粮绝。
陈培兴和他的干部们躲在破碎的窗户后面,紧紧握着手中的刺刀。
一旦敌人破门而入,这些人将不再是书记、文员、医生和教师,而是死战到底的战士。
而在敌军眼中,这一战不过是即将开瓶的胜利果实。
前有四百外籍雇佣兵持枪步步紧逼,后有千余土匪虎视眈眈,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。
负责围攻县政府的,是两个匪首林显与何康民。
他们站在一处临时指挥部的高台上,冷眼观战,等待着县政府最终沦陷的那一刻。
只是,这注定是痴心妄想。
清晨六点,山脉的五个方向同时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。
敌人惊愕抬头,瞬间乱作一团。
雇佣兵尚未来得及反应,只见从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,分别突入一支支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突击队,另外一队则从中轴线直插指挥部后方。
这正是战斗英雄们精心筹划的“五路突袭”战术。
68位战士分为五组,沿着地势分布的街巷、河堤、竹林、山道迅速逼近县城,一声冲锋号既是信号,也是威慑。
他们并未依赖密集火力,而是巧妙利用地形优势,形成犄角之势,将敌人牢牢锁在包围圈中。
其中最关键的第五组,由副团长杨贵生亲自率领,他们悄然潜入县城西北角一处废弃火柴厂后方,那里正是匪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。
敌人自恃兵力强大,指挥部设得靠前,却忘了对后路防备。
炮声轰鸣,硝烟四起,指挥部大乱,林显失联,何康民慌不择路。
各路土匪失去指挥,阵形崩溃,雇佣兵也因通讯中断,成了群龙无首的孤军。
逃得快的钻进巷道,逃得慢的,倒在突击战士的火力之下。
此时此刻,整个战场已完全反转。
原本压制政府的敌军被拦腰截断,医院一侧的匪徒尚未集结便被击溃,中学方向的匪团长因为儿女被困校园而不敢强攻,反被老师学生以火力拖住。
县政府这边,则由第五组从后门突入,一举歼敌三十余人,直逼政府围墙外的最后火力点。
不到两个时辰,整个战局便告一段落。
这场原本注定悲壮的保卫战,也因这五路突袭,成了一场经典的逆袭战。
士兵们从火光与血雾中走出,面孔黑黝,眼神坚定,胸前功勋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后续的剿匪行动,也从此获得先机,敌人再不敢低估我军意志,再不敢轻言围城。
他们知道,乐昌有68个战斗英雄,他们更知道,68只是一个数字,那背后,是整个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骨气。
终结乱局
乐昌县城的硝烟尚未散尽,尸体尚未掩埋,英魂未曾安息,有百姓伤亡,也有战士壮烈牺牲。
通讯恢复后,战斗英雄们以一敌众的传奇战绩,在野战军内部迅速引发高度关注。
于是高层领导决定,将早已准备投入海南岛战役的一支整编师,临时调派至粤湘边境,目标只有一个,彻底剿灭盘踞在大瑶山的土匪残部。
剿匪部队以战斗英雄为核心力量,前有英雄先行者,后有正规军压阵,采取“拉网围剿、分区突击、山谷封锁”三路合击战术,将整个大瑶山封成铁桶之地。
山道被封,水源被截,粮草被毁,昔日猖狂跋扈的匪首林显、何康民等人,一个个如困兽一般,被逼至绝境。
他们试图组织反击,甚至从香港请来的外籍雇佣兵也被重新召集。
但在我军精确的火力覆盖与地毯式清剿下,那些雇佣兵,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纸老虎。
乐昌地势复杂,山脉重叠,溪涧纵横,清剿工作极为艰难。
但我军部队纪律严明,兵分多路逐村搜索,凡村寨空无一人者,不扰、不焚、不掠,而是修缮门窗、清理院落、张贴春联。
他们用行动告诉百姓,解放军是他们的保护者,这是真正人民的军队。
这一举措,不但让百姓安心,也悄然动摇了匪徒的心理防线。
最先动摇的是一批被迫从军的青壮年,他们多为村中乡民,被裹挟入山。
如今见我军秋毫无犯、春风化雨,纷纷下山投诚。
他们带着枪,带着粮,也带着一纸纸匪首罪行,争相揭发主谋,期望宽赦自新。
尤其是九峰乡,一夜之间竟有75名原国民党校级军官走出深山,主动缴枪,宣誓弃暗投明。
这些人或曾受命于薛岳麾下,或曾任职于国军地方守备部队,后来藏身山林。
现实已经告诉他们,旧世界已崩塌,顽抗只会自取灭亡。
那些罪行累累的匪首更不用说,属于他们的判决在等着他们。
剿匪行动持续整整一个月,至五月初,全线结束。
战果之丰,令人震撼,缴获武器无数,匪徒伤亡与俘虏数千余人,匪巢尽毁。
从此,乐昌再无匪乱,百姓重归宁静,这里终于迎来久违的和平与秩序。
那些英勇的战斗英雄,那些保护家园的普通百姓,那些挺身而出的人,无一不被深深铭记。